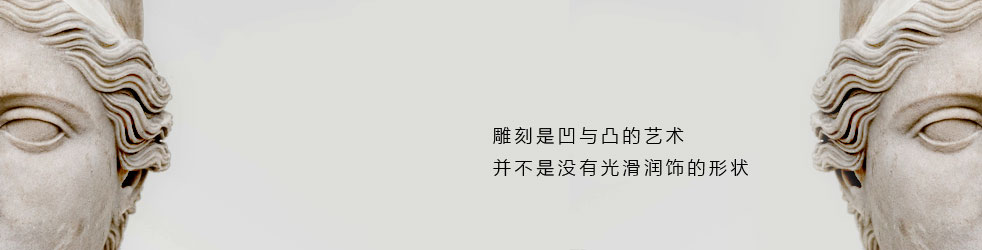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美术学院:当代美术军团的大本营
——论学院于当代美术之意义
自从人类的美术行为由众说纷纭的各类模式起源说,走向有了确切文字或图像记载之时起,美术活动就被证明是一个群体性的活动。因为它始终是伴随着宗教、巫术、祭祀、建筑等与人类自身安妥灵魂与身体相关的活动在进行着的。
共同劳作是原始先民共同生存的需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所谓美术活动同样如此。当关乎生存大义之所须的大美术活动必须要进行之时,共同参与是保证计划得以实施的前提与基础。于是同一群体中的劳动分工逐渐分化出带有职业特点的群体,设计师、科学家、哲学家、美术师或画家与雕刻家等等,便成为了专司一职的行家里手。这些身怀技艺的人在传承赖以为生的“手艺”时,也逐步由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集团式向以技艺资质为号召力的课徒式转化。于是,含有现代教学方式的传艺机构——技艺工场、名人教室、工作室及其师生关系等的产生与确立,拉开了美术院校产生的序幕。由西方而东方、由古典而现代,直至今日的美术院校以及设有美术类教学内容的其他院校,在今日的中国至少有一千所以上。在如此庞大的教学机构群面前,学院,这种专门在教美术与学美术的对应互存关系中疯狂竞争的营垒,其竭泽而渔式的扩招运动,使讨论其与中国当代美术之关系的努力,显得极为无所适从,甚至多余!因为普遍的求生诉求已经扭曲了以往采行的精英教育的路线,这是无法断言孰忧孰喜的局面。 但是仿佛以往的精英们不甘于在此局面前的无所作为,于是希望梳理出显示得失的具有定位性质的结论。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一、 当代美术群体的学院背景 美术院校在中国的历史不过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出现过“美术学院”的称谓,但不是以现今学院招生的概念。类似于现行的“画院”、“美术院”。)而严格意义上的以“美术学院”名义行世的历史也只有50余年。在这50年间,无论其师资背景是来自本土的、欧洲的、或是前苏式的,最终都成为了那些活跃在当代中国不同年龄层面的美术群体们的教导者与启蒙者。时至今日,老中青队伍仍然活跃异常,凡有重大事项,均可看到毕业于50年间任何一届的三至五代人共商大是的局面。而正是由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美术的繁荣局面。 于是,我们应首先廓清:“当代”是什么概念,是时间概念,还是风格概念? 若以时间论,凡活跃于当今中国之美术活动中的任何年龄、任何风格的成果形式,都在“当代美术”的范围之列;若以风格论,那便是特指在参照了西方当代艺术及美术观念座标下的、迥异于架上写实手法营造画面的、并且逐步消解了画种边界而走向综合的样式。 但是无论上述两种关于当代含义的现象如何不同,都不可回避一个巨大的事实,即这支包括了老中青数代人员在内的美术大军的学院背景。正是学院培养了他们,造就了他们! 认识学院背景,应据以下推算: 1、文革前的17前间,全国八所美术院校每院每年毕业50人,17年间共计6600人; 2、文革后的1977—1987年10年间,每院每年平均毕业200人,以10所院校计,共约2万人; 3、1987—2004年的17年间,每院每年平均毕业400人,共约68000人。 三阶段相加共154000人。 事实上,自建国之前,许多师范类院校,各种专科院校、艺术院校美术系、美术科、美术专业等所培养的毕业生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尤其是在近5年来的扩招运动中,几乎所有院校都有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设置,仅每年毕业的美术类学生总量至少应该有3—4万人。总数应该至少在60万人左右。 但是,所有美术学院及相关美术专业的教学模式,在中国几乎是一致的。如必须通过素描、速写、色彩几个科目的敲门砖式的练习,达到专业院校与其他各类设有美术专业院校们的统一标准。过去招生中尚有根据不同专业需要而设定的不同门类性的专业考试,但近几年经过整齐划一地“整合”,的确是“简洁明快”了许多!无论考生什么兴趣与基础以及报考的什么专业,一律是素描、色彩定乾坤! 上述之现状,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美术群体,在世界范围内是巨无霸;二是其群体是在共同标准制约下产生的、非常具有趋同性的学院背景。正是这种既巨大又一致的、具有着大同小异的所受教育质地的影响,已经像我们所了解和知道的那样决定了以往中国美术的基本状态,并将继续对中国美术事业的未来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美术科班出身的这支庞大队伍,其共同点是:具有着一般或是高度精确的写实模拟能力,掌握着再现物体三维空间感觉的技巧与方法,具备在自然条件下,用写生的办法捕捉出对象瞬间状态下的彩色和动作的能力。在结束这种科班学习的时候,一般都能够通过使用照片或模特来完成一件或多件、以写实样式为主的毕业创作。一般情况下,当这种教育程序运行至此时,“产品”即告马上可以“出厂”。五十年来,全国各地至今如此。 上述的教育模式与成果口径,造就了中国美术界长达100年来基本一致的写实风格占主导地位的总体态势。但这只是中国美术学院背景下的队伍规模与教育模式。另一层次的影响还在于,中国人特有的师承心理所形成了巨大的样式单一雷同的严重后果。在中国美术家的名份记录中最乐为人道之处便是远宗某某大师、近承某某面授……。在进入了具有现代教育模式与教育精神的中国现当代教育机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所学之法系于某师某派之技术样式,往往是居然能够延续多年,历经多届学生、并形成群体性共同追逐的目标。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百余年来的美术教育中屡有发生。被最多主动标榜有直接或间接师承关系的两位美术教育家便是林凤眠与徐悲鸿先生。 实际上,两位大师恰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果,而后来者都以曾经受教或承袭其衣钵为荣耀!仅管后来者却鲜有出其右者的影响力与成就。但对师承关系的申明则十分重视。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全国与地方各层级的教育圈子中,都有以标榜师承关系为划分学术势力范围的情况发生。它坚持纵向的宗法性,而不鼓励横向的多元性。这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制与封建残余思想的无奈合流。 综上所述,无论上一个百年纪元中,还是当今急剧扩招下所形成的局面中,学院背景是当代中国美术群体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基础,这便决定了中国现当代美术的总体走向,并深刻地具有着“学院”的烙印。 二、学院教育形成的学术背景 虽然学术并不为学院所独有,但学院必依学术以立身。学院教育模式的本质即是以相对科学的教育方法,较为恒定的教学步骤、较为稳定而严格的教学程序,以及较为整齐划一的教学要求,从而使学生们的技能性与认识能力得到普遍性的提高。于是,相关的学术问题便相伴而生。 总体看来,从来的学院中所面临的学术问题,即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认识论层面;一是方法论层面。 在中国的美术教育理论领域,应该说是方法论盛行的天下。这在中国有着深厚的遗产基础。中国的诗、书、画理论积淀巨富,但绝大多数讲方法、技巧、步骤等等,少有涉及思想、精神、观念、审美等问题,即便偶有论及,也多是一闪而没的只言片语。 这在中国的美术学院的短暂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清末民初,西洋或东洋美术教学体系,也首先是作为一种新方法而去学去引进中国的。纵然再向上推数百年的明清传教士们的作品,也是于“法”的层面,融入中国原有的国粹样式中而获得中土人士认可并得以流布的。后来的中国美术教育,以全新的“写生”(石膏、风景、人像等)法,全面移植了西洋绘画的教育模式,同时也确立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学堂”体系。 由“学堂”而学校、而学院、而大学等称谓的更新,说明这种体系的逐步扩大。而就美术学院或院校来说,以传授方法为最基础教学目的的原则,始终未变。在中国的美术院校中,崇尚技术是根深蒂固的诉求理念。而评价体系(诸如评分标准、印象评价等)也多以某专业技术能力的高低而为伯仲之分野。流行并且崇尚的也只是技能加方法的相关理论。所以美术院校的学生大多不读书,尤其不读专业之外的历史、哲学、文学、文化史,以及有关艺术认识论方面的著作。这应是当下或当下之前的学院教育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背景状况之一。 构成上术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当今普遍认为:艺术人才是以具备某种技能技巧而存在的专业人才,故主动降低文化准入门槛是普遍的做法。社会广泛流传的“学习差,上美院”的风习,不仅属实,同时也是美术院校甘愿接收文化差的生源,自取其辱的事实所造成的。 正是由于文化素质单薄、肤浅而形成的学习群体,加之教师队伍多数人的相应缺失,使教与学二者之间并没有产生不相协调的反差。相反,以技能为崇尚诉求的教学双方,毫无障碍地可以构成支撑这种教育现状延续下去的主体。这是当今学院教育形成的学术背景状况之二。 但是既为学院,必然有一批学人的汇聚。这便是一批从事非实践性或说是不以技能性实践为主的专业史论专家,或是以学报、刊物为工作园地的,并且有着史论学历背景的专业人员。由他们构成了中国美术院校中最具理论色彩与学术色彩的人文背景。于是,学院教育中的学术焦点以史论为主轴,兼及美术评论,以及美学研究领域。其成果除各种门类美术史著作外、诸如画论研究、美术批评、美术考古等领域成果,是其主导产品;其次是以论述国外美术现象、美术家传略、美术思潮等内容为主的贴近前沿状态的他山之石类的成果。再之即是以武装了新异思想、并以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作为其论述支点的评论领域。二十余年来的中国美术界,以美术理论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已然形成了不同年龄层次的梯队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论述者和被论述者互相成就了对方。 上述之种种,虽不能尽归为学院范围,但绝大多数学术理论成员产生于学院是无疑的。所以,我们论述学院之于美术教育及理论群体之时,便可看出,这样的群体及其学术背景所具有的学院烙印。 首先,史论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来自于学院。据不完全初步统计,百余年来产生的关于美术的学术性史论著作计有《中国绘画史》约五部,作者分别是秦仲文、潘天寿、黄宾虹、郑午昌、俞剑华;《中国美术史》约四至六部,作者分别是胡蛮、郑午昌、陈少丰、李浴、姜丹书等;以中国绘画思想、材料、画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有吴茀之的《中国画概论》、蒋云怡的《中国绘画材料史》、傅抱石的《中国绘画理论》、《中国绘画研究》、黄宾虹的《中国画学史大纲》、胡蛮的《中国美术的演变》、陈士文的《中国绘画思想》等;以门类美术及技法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有:郑午昌的《中国壁画史》、吕凤子的《中国画技法研究》、黎葛民的《图画基础技法概论》、王子云的《中国雕塑史》、郭味蕖的《中国版画史略》、陆地的《中国现代版画史》、陈之佛的《图案构成法》、潘天寿的《中国书法史》、傅抱石的《中国山水人物画技法》、席德进的《台湾民间美术》等;介绍或研究西方美术的成果有:陈之佛的《西洋美术概论》;倪贻德的《西洋画概观》;周碧初的《西画概论》与《近代法国画展源流》;陈依范的《苏维埃艺术与艺术家》、《苏维埃绘画艺术》、刘汝醴的《苏联艺术史》、《古埃及美术》、江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西洋名画欣赏》、高剑父的《印度艺术》、王子云的《从长安到雅典》等等;而从中西方美术比较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有:陈士文的《中西绘画比较》、《近代西洋画派与中国艺术》;李仲生的《二十世纪绘画总论》等;而作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的身份,集一生学养体验而留下个人美术文论的著名人物有:刘海粟的《国学真诠》、《刘海粟文选》、伍蠡甫的《谈艺录》、《欧洲文论简史》、《艺术美学文集》、卢振寰的《北宗画法》、胡佩衡的《画笔丛谈》、《冷庵画诣》、夏敬观的《忍古楼画说》、高剑父的《中国现代绘画》、李可染的《李可染画论》、黄宾虹的《虹庐画谈》、吴作人的《吴作人文选》、蔡若虹的《美术论文集》、张望的《美术评论集》、刘开渠的《美术论文集》等;在整编中国古代画论方面最为功丰阙伟的是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俞剑华的《中国画论类编》;上述数据尚不包括近二十年间美术院校中的许多中青年学者的最新成果,但已经为我们树起了一道中国自诞生美术院校起,在学院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学术风景线。上述众多著作成果的作者,无一例外地是百年来毕业于国内外美术院校或任教于美术院校的著名画家、雕塑家、教育家与研究家。 由此看,学院学术的特点应概括为:一是具有学术纵深感;二是眼界开阔;三是注重横向比较与纵向断代的深入研究;四是理论阐述与技法实践兼顾等。一般的过程大致是由习画入手,逐渐由实践中引发对相关理论的关注,转而投入精力,著述与实践并举。如潘天寿、傅抱石、郭味蕖等既是著名画家,又都有各自的《中国绘画史》的专著,其中傅抱石编著了《中国美术年表》,郭味蕖则编著了《宋元明清画家年表》,而一位女画家陈小翠则有《明清500年画派概论》的著作,这都是由浅及深,由点至面式的学术走向;百余年来的中国美术新军,在为传统艺术洗心革面的同时也是具有国际眼光的排头兵!在一个多世纪中,无论西洋、东洋,许多画学青年负芨远行,学术触角遍及人类优秀文化的许多方面,如陈之佛、倪贻德、周碧初等均有关于西洋美术的史论专著等等。除此之外,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兼而顾之的复合型学术走向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傅抱石既有绘画史的专著,又有山水人物画技法的专著,谢稚柳既有关于敦煌艺术的专门研究,又有关于水墨画的技法与专著;另外,王子云先生油画、雕塑实践并举,同时又从事中西美术考古成就卓著等等。总之,学院美术教育的烙印,以上述诸多的学术成就者的巨大事实,证明了学院学术的显著特征。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上,我们的上一代或两代三代前辈们所特具的文化素养与时代风潮相得溢彰的优秀结果。 二、 学院之于当代美术的主流地位 中国的当代美术的发展、演变以及观念的更新,从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过或是脱离过学院的巨大存在与影响,甚或是认可。因为百余年来,美术教育的普及,几乎是所有美术人必经的学习途径,而学院教育的基础累积也是所有美术人能够活动于美术领域的最低准入门槛。所以,学院教育的全面影响是多方面和巨大的。 首先,学院带有普遍性与强制性的教育模式不仅体现于通过逐步累积而使学生绘画技术不断提高的层面,而在建立艺术思想理念、开阔学术视野、强化艺术创作实践等层面,也具有着巨大的导向性和规定性。这便使得学生在通过由获取基本技术到进入思想观念表达的总体过程中,牢固建立起了因果关系的程序模式。 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教化、致用,是从古至今的主导思想。中国提出审美观念极早,但却以美育入教育至晚!但当中国一俟引入新学以来,相对科学的教育内涵便迅速被西学中用的理念所统领。美术同样如此,它虽以西洋科学观察法、色彩法、技术法而授教,但都在美术之功用与艺术之目的的层面,依然是“中用”的致用法。由为民生、为大众、为政治、为运动、为工农兵等等不同历史时段的表象的更替及演变观之,客观上形成了当今中国美术院校教育的独特走向与历史特征,同时也构建起了一套由学习技术向创作艺术循序渐进的模式。具体说即是基础学习+专业学习+体验生活+毕业创作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首先是使受教育者能够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其次是建立起通过走向生活才能获得创作成果的观念、并将其固化为一种规律而加以遵守并扩至更大社会层面;再者是全社会都在普遍认同并鼓励由此路径而产生的成果才是美术创作的正途与正果。相应的评判标准也长期锁定在以此建立起的价值观上,即推崇有生活真实感受或者再现生活场面的、尤其是具有重大革命历史意义与宏大叙事风格的作品,备受关注。 此种模式的弊端在于:首先是因目的的锁定是反映生活,所以为“反映”而储备的知识与技术是描摹客观物象的准确以及再现的能力,所以形成了长期风格雷同,手法单一、教学模式大同小异、只注重共通性,而忽略或消泯个性的教育结果。 其次是导致了长期以来中国美术家大多数人的言说角度的隐化与淡化。也即为他人而说他人,结果是在为观众呈现出一幅被描绘者的生活状态图景,而自己仅仅是一位“转述者”。在这样一种转述的过程中,作者的风格、心灵等等本应得以外化为视觉样式的隐性精神,只有被遮蔽!个人化的张扬空间微乎其微。于是,导致了中国美术院校教育所形成的另一特色。写实技术走遍天下,风格样式大同小异。 仅管如此,我们仍应看到,近二十年来中国美术观念的变化是巨大的。言说角度的转变正在许多青年美术家中产生。向他人说自己、或向自己说自己的各类情形都在发生,并逐步获得着社会之认同。但在美术院校的教育实践中,似乎还在烙守着旧模式,远未产生出多样性的变化。 上述的既有优点又存在缺陷的中国美术教育,在快速膨胀的规模增殖中,老旧的模式也在随之而延续。当今,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与美术相关的行业中,由学院所教授给他们的这套观念与模式也同样在传播。不仅在今日的多如牛毛的各类美术活动中,他们客观上形成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即便是在日常的知识渗透性的活动中,也同样如此。 于是,中国的美术院校教育及其产生的效应,是中国当下决定美术主流走向的重要因素,也从而使院校所确立的价值体系确立为弥漫于整个社会中的美术评论标准。 学院的存在是形成巨大势力的前提。由于各地美术院校所处地缘分布上的网络化优势,以及近年来由原有专业院校而扩展出的泛美术专业化的急速增长,各院校之间的高度统一,假以行政协调的手段,似乎可以在教学方略与施教方法等方面在短时间内迅速构筑起联动反应,从而使发生于中国的许多美术活动或是美术主张都操控于美术院校的影响之下。换言之,中国美术之动向,毋宁被视为美术学院之动向。这样庞大而牢固的运转于国家机器中的铁打的教育机构,毫无疑问地左右着代表国家地位的话语权。 正是由于体制内的优越性所使然,全中国的美术院校以及开设美术专业的各类院校,从来没有忧虑过生源问题,也从来少有开办不下去的烦恼。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美术学校,数量惊人,规模、水平也参差不齐,但绝大多数是今天看来属于体制外的民办性质。那真是一种适者生存的与市场完全接轨的运行机制。各类学校虽存活期不一,学生多寡不同,但决无统一的教纲与共同的、一致的、带有规定性的学术主张!也极少有凌驾于著名画家、教授、学者艺术理念之上的、弱化了个人偏好与个性特色的统一标准,这便为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与存在空间。同样,教授的选择与延聘或是去留更无当今如此这般的复杂与刻板,等等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近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在现今已被格式化了的程序中几乎是已办不到的了! 但是无奈!体制内有丰厚的待遇及无后顾之忧的住房、后勤保障,有限制人员流动并与整个体制相配套的、使许多人不得不考虑的住房及子女就学等方便条件,有由整个体制而维护的教授个人的永久性权威,另有各种各层次的声誉待遇等等!从而使体制内充满着诱人的光环,也迫使些许的人们以占据体制的制高点为其战略目标,仿佛具有了体制内的话语权便代表了整个体制。 由许多的占据制高点的人们所构筑的、以代表体制内最大利益为前提的美术教育同盟,自然将自身无可替代地强化为主流社会中的主流角色。这是无奈但是非常好的战略诉求!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美术院校或是设于各类院校中的美术教研机构,在当今已不单纯是一门类性质的教学单位了。它在事实上不仅于制造美术人才的方面是绝对的主流,而更重要的是假体制之强势而成为制造规则的主体。 结 语 美术院校的资源优势是提升自身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院校间的横向联合是全国联动互补的前提保证。近年来,由院校发起、组织、倡导举办的各类展事、研讨、论坛等活动,远远超过了由社会团体举办的活动。简言之,院校活动在膨胀,社团活动在萎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由此可以推断,随着越来越多的院校加入开设美术专业的行列,以院校为代表的中国美术阵营也将日益壮大!美术学及相关学科的体制认同,为维护学科尊严、梳理学理规范、深入展开理论研讨等,都提供了更大的拓展空间。同时,以院校为人才基地的资源优势,能够始终确保人员队伍的充盈饱满,加之有雄厚的资金保障,有刊发各类成果的刊物等等,故有一天,中国一定会产生“中国美术院校美术家协会”。 我们当然呼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发表评论
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