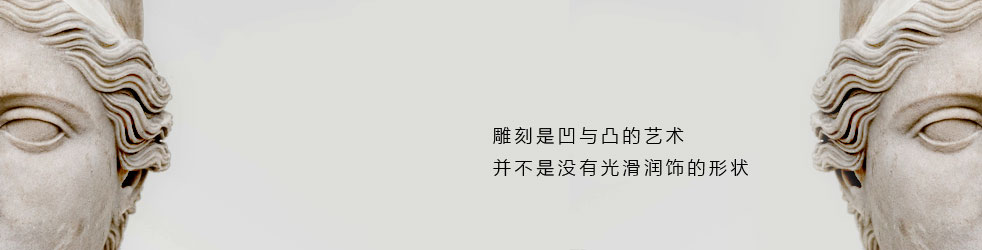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二十年前,我在西安美院雕塑系临近毕业的5月份的某一天,收到一封白纸红字印着《美术》杂志社字样的一封信,内容是一封兰色油笔手写的会议通知:说我参加他们征文的一篇文章,已编入当年第六期,向我祝贺!并邀请我去湖北的神农架参加“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会期20天。叮嘱我要多带衣服,并穿防滑鞋云云。
依当时《美术》杂志在美术人心中的地位,神圣不可攀!居然我有文章要刊发,并去神农架那么神秘的地方登山开会!这真是一件令人喜极的消息。这一年我26岁。
于是,我用三天写完了毕业论文,匆匆硬座到了武汉,按址找到了会议接待处。当晚,会议一行便乘上了武汉行经郧县的火车。工作人员一再解释只有上铺了,不好意思!其实我早已受宠若惊,因为我这是平生第一次进卧铺车箱。首站目的地是武当山。一行来自全国的老小代表中,就我最小。在漫长的登山过程中,才知道这里边有《美术》杂志社的何溶先生(中国当代美术革新的发动机式人物)、锐意革新中国水墨画的周韶华先生、现在中国画研究院的张士增先生、葛晓琳女士;北京大学的叶朗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沈鹏先生,还有多位当今在中国美术理论界执牛耳式的人物。他们的今天,莫不与本次会议息息相关。
自武当山的金顶下来,便真正进入了神农架深处的一座小镇松柏镇。在离镇上约一公里的山坡上,孤立地建有一座崭新的三层小楼。据说这是为曾经要来此进行科考的德国专家们盖的,但是却没来。而我们则成为了这座建筑的第一批客人。
20天的会期,在人类会议史上,无论如何都应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然而此地很好!推窗凭栏,俯仰远近,莫不满目苍翠,人在画中。这一群山中“闲”者每日便坐而论道,不计东西。当时中国美术界存在的种种禁固,出现的种种新异,统统俱在议论之中。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与会者在如此从容的会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次晚饭后的散步,大家便在路边的溪流中捡石头。沈鹏先生与我并肩闲话,他告诉我:这次征文收到文章100多篇,写雕塑的有两篇,认真比较了一下,你的这篇内部逻辑很强,希望你多多努力,将来可做理论的发展!二十年过去,这一席话,那一幕情景,犹如昨日。但我终未能彻底地向理论发展,虽然也写了六七十万字的东西,出了几本“著作”。但只小可耳。
那时的沈鹏先生像现在一样瘦弱。他每天寄情即兴吟古体诗词若干首,晚上便以行草写出。十余天后,他推我房门,点点头、招招手:小陈,你来。我忙随他到房间,他拿出一幅字递给我:这是写给你的。我打开一看,上书“转益多师为我师”。他怕我不懂,又给我解释:要扩大学习的范围和眼光……。他向每人赠了一幅字,何溶与周韶华先生也向每人赠送了一幅画。这些墨宝如今我都珍藏着。只是何溶先生已作古十余年了。这是一次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标志性的会议。是经过十年文革压抑之后,又迎来迅猛复兴时,美术理论界调整应对平台的会议,是一次注定要向未来20年间推出一批优秀理论家与批评家的会议。
二十年来,还是这次会上的人最亲切。大家不论长幼,以朋友相看,尽管现在沈鹏先生是全国书协主席、叶朗先生是北大著名教授,三个系的主任,还有贾方舟、彭德、皮道坚等先生,如今见面,总要说到那次会,总要说再也找不到那次会议所结下的如此长久亲情的感觉了.那次神农架中的会议。
二零零三年追记于长安
发表评论
请登录